遗忘间
2005-02-16 21:22 | 噩梦
5:30 PM
没什么。
我对自己说没什么。我是漠然。
6:50 PM
冬天就是会这样,夜晚不断地提前提前再提前,努力地压榨掉白昼的每一丝阳光。黑暗的工作比许多人都要勤奋得多。
就这样,天边的残光模糊地颤抖跳跃,可怜兮兮。
或许是黑夜,把我浇灌成一棵独立生长的倔强植物。手中的空酒杯,在灯光下起舞,说不出是为谁而泣。
三年前的时候小沫走的时候很难过。我们。
是个夏天。我记得那个下午她忽然来到我家找我,说她要走了。那时的天很阴沉,空气里压抑着浮躁炎热的水分子,我们就在楼后面那堵灰色的大砖墙面前告别。墙对面的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我们一起,听见时光断裂的声音。这回忆断了,便再也寻不回来。对此无论是我还是小沫,都明白。但我们也同样都无能为力。
几分钟,大滴大滴的雨点忽然落下来。玩耍的孩子们慌乱的躲进屋檐下,不知所措的望着街上瞬间卷起的汹涌溪流。
我对她说,要走了,要好好过,要记得回来看看。
忽然就哭了。
我明明看见小沫张开了嘴唇,那久远的声音却被大雨和时光湮灭,不能辨认。直到那时的天,那灰色的墙,高大的树在记忆中缓慢褪色,依然辩不清小沫最后对我说的话。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时光流逝,此前做过的一切便无法弥补。我们此后没有再联系。
回忆就这样中断了。
7:00 PM
天黑黑,我不知道,是不是又要下雨。
8:20 PM
妈妈打来电话,和往常一样说食物还是在冰箱里面,今天晚上她还是不会回家。
我很平静听她说完这些,然后挂了电话。若是以前我会发很长时间的呆,掉眼泪,然后问爸呢,爸在哪里呢?现在我不会再那样问了,因为那样很傻,因为那样妈妈也会伤心。我比以前懂事了,只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发很长时间的呆然后安静地掉眼泪,只不过不会吵也不会闹。其实我还是很软弱,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不过是装作很坚强罢了。
想起沉若对我说,漠然,你要知道,外壳越坚硬的蜗牛,里面的身体就越软弱。
我小的时候爸就和另外一个女人走了,留下我和母亲。还好母亲很能干,自从爸走了以后她真得变坚强了,坚强到一个人让我们两人这个破败的家维持着不错的生活。只有我一个人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他走的那个晚上。不知多少年以后我开始告诉自己要坚强,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唯一的支柱。但我能做到的,仅仅只是不在妈妈面前掉眼泪而已。
其实爸长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是迷恋于“父亲”这个称呼。后来的时间里夏远告诉我说,有些人有些事情是会一下子突然忘记的,因为那记忆的主人不再想留着它。再后来的时间里我开始相信这句话。
9:10 PM
桌上随便地堆放了牙膏状的颜料,没有削完的铅笔。未完成的画布还挂在墙上,干涸的厚重油彩,在记忆中等待褪色。
墙上的那幅是在小沫走之后画的,一直没有画完。记忆中小沫给我看过的画面一直都找不全,记得是一片无边的金黄麦田,穿着裙子的女孩在其中奔跑,稻草人在田中安静地守望,身上栖满了乌鸦,天空是一片空旷,浮云在发光。
小沫喜欢画画,于是后来我也喜欢了。
仅此而已。
9:40 PM
对待一件事情,沉迷是致命的。
比如回忆。
我现在时常会想起小沫,想象她现在过得怎样。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我的话,也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最后对她说,要走了,要好好过,要记得回来看看。其实就算她回来过,我也早已经搬了家。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感情,改变回忆,以及改变与之相关的许多事情。纵使了解,我们也对此无能为力。
唯有沉迷。
9:50 PM
我出了门,去买一包烟。
10:00 PM
最后付钱的时候我才发现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杯,沉迷会使人在恍惚中忽略自身现在的状态。这正是它的危险所在。
手机响了,夏远的短信。
放寒假了吧,过年的时候你们一家来东北吧,两个人太冷清了。
好的,我跟妈说去。
我带你去看海。
你说,时间真的能改变一切么?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但它真的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无能为力。别想太多了,漠然,你还是个孩子。
恩我知道了。
夏远是我上初中时的朋友,高大清瘦,笑容干净明亮,大多数时候都很沉默。以前我们经常到各自的家中去玩。家长互相之间也因此熟络了。后来夏远回了东北的老家,我们两家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逢放假过节的时候,我和妈偶尔便去他家。夏远的父母也很热情,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家的人一向是不容易结交到什么朋友的。
夏远和我都长得很高很瘦,我们也同样都很沉默。但与他相比我永远还像个孩子。
0:50 AM
关机睡觉。
8:40 AM
我是被手机的铃声吵醒的。才想起昨天晚上沉若发的短信一直都没有回。
认识沉若的时间不长,可能也就半年的时间,却是很快乐的半年。每天放学我都会送她回家,有时候会用手指捏她的鼻子,拍她的头。她尖叫着追打我。我就抱头假装求饶。然后我便在一旁看着她笑,声音会一直传到街的尽头,放肆而孤单。
有时候会逼问自己究竟把沉若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却问不出个究竟。我们都是这样,带着各自的伤口不肯脱身,而企图内心挣扎的人是孤独的。我们也都是这样在互相温暖着,安慰着。
或者说,我们相爱。
这只是个太稀松太平常的字眼。
9:00 AM
草草洗梳,发呆,看窗外苍白的天空,像白色的洞口。
然后回沉若的短信。
我失神了。
哦没事你总是这样。
出什么事了?
没有。
11:30 AM
中午妈妈回来了。
我说夏远约咱们去东北,妈就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回去睡觉,什么话也没有多说。看得出来她很累。
外壳越坚硬的蜗牛,里面的身体就越软弱。
忽然想起这句话,沉若说的。也不知道她是在说我,或是说自己。
1:00 PM
整点,正午的阳光激烈。鸽子飞过对楼的天台。
1:10 PM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在我的脑海中是一片纯白色的记忆。我和小沫住的两栋楼是对着的,鸽子也是那样飞过各自的窗前。
羽毛落下来,飞鸟歌唱。
飞鸟路过只用了几分钟。
几分钟,一次昏厥。
几分钟,几个生命诞生,几个生命沦丧。
这几分钟在大多数的生命中不值一提。
直到那时的天,那灰色的墙,高大的树在记忆中缓慢褪色。偶尔起床还会看到一对鸟儿在快乐的飞翔,心里就会有最不可言说的熟悉隐痛,低下头让泪水稀薄了颜料。
画布安静地挂在墙上,一张CD反复播放。
1:30 PM
沉若把我约到街边,她说,漠然,我们分手。
那一瞬间飞鸟如同浮云蔽日的在冬天里飞过,穿越时间穿越冬夏也遮蔽了沉若那时的面容。
为什么?
不知道。
还爱我么?
爱。
那我们不要分开,我们没理由分开。
那就可以在一起了吗?
恩。
多久?
我不知道。
天空和日光变得很沉默,城市在那一刻瞬间灰白。指尖冰凉,积雪温暖,掉了漆皮的指示牌有四个方向各奔东西。叶子飞走,树影稀薄,没有人知道何时该分开,飘去何方。被拆除的砖头安静地躺在地上,路过的人也不会多看它一眼,寂寞就忽然来袭。只有冬天一直寡言,用寒冷诉说着孤独和创伤,尘土飞扬。
一场稀薄的幻觉快速播放,然后我听见她说。
好吧。
5:00 PM
夏远告诉我说,他已经回来了,明天来看我。
夏远。这个名字是个魔咒,她和他在三年前的夏天走远。一片炎热潮湿的气息。
眼睛发涩,像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隐痛,来自一个幽深的伤口。
11:00 PM
早早睡觉。明天早上夏远就会来。
7:50 AM
第二天下雪了。
夏远变化不大,还是一样的沉默寡言。他进屋的时候,我一回身看见墙上铺展开的大大的画布,眼里就隐隐的痛。
我问,夏远,你还记得小沫么?
夏远盯着那幅画不发一言,眼里氤氲一层灰蒙蒙的雾气。张口想起说些什么,终又禁闭双唇。窗外一片厚重的银白色,天空苍凉沉默。夏远低下头,颈间一阵冰凉的闪光。粗重的银制项链,坠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像是某种束缚,某种桎梏。
不记得了啊。
夏远走过去抚摩那画布,试图回忆些什么,三年前的夏天同样也是他离开的季节。我开了窗子,几片雪花飘进来,落在画布上就融化了,夏远眼里仍是厚重的大雾。
还记得三年前楼顶天台的飞鸟吗?
夏远忽地停滞,回过头时眼里冰雪散尽雾气消亡,又是曾经的干净明亮。接下来一个微笑。
记得呀,不是我们两个人喂的吗?
那一秒心跳漏过一拍,窗外光芒瞬间绽放忽又黯淡,最终一片灰白色。既然有些人有些事情是会一下子突然忘记的,因为那记忆的主人不再想留着它。那么什么时候我会想到放弃。
11:30 AM
中午饭以前夏远走了,我独自接沉若去吃饭。
我把三年前我们住的地方指给她看,心里一片荒芜。看吧,看吧,什么都没有。沉若冰凉的手覆盖上我的眼,就痛得难以自制,眼睛最深处幽深的伤口暗潮涌动,最终碎成一朵朵模糊的水印。然后眼里大雾弥漫,阳光透过沉若的掌心一片暗红色,暖如地血。手指的方向两座楼孤傲地对立,不见飞鸟,不见夏天的影子。手指寂寞的蜷缩在一起,形成一个可耻姿势。
忘了那些好吗?为我。
树影稀薄,我看见阳光下空气中那些缓慢凝滞的柔软灰尘,心里就躁动不安。我知道决定会影响很多事情,但忘记绝不会说到做到。
最后我只说,让我回家,我想回家。
我很傻,傻到自以为很聪明。
1:30 PM
我晕倒了,现在是在沉若的家里。
我和沉若中间摆着一个桌子,两杯清水,过了正午的阳光开始疲惫。
冬天像一个无限扩大的白色洞口,长的无边无尽,我们被吸入其中无法自拔。路途坎坷有些人散落在了天涯。
我喝了口水。
你说,冬天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傻东西,你随时可以出来。
你会帮我么?
不是不会,是不能。哪怕是我,也不能。
洗手,然后打开窗子。阳光开始与我对峙在窗户的两侧,彼此都那样的沉默。空气很凉但下午光线充足,只是天空的颜色有些苍白和我一样。沉若在背后轻唤我的名字,漠然,于是我回头。隔着雾气看到沉若的长发间隙在发光,就伸手去抚,又想起小沫亚麻色的短发在夏天的阳光下沾上了颜料。
我说,我要画最后一幅画。
好。
2:30 PM
沉若也学过画画,在她家里就可以。
我用铅笔,画了一堵高大的灰色的墙,夏天的树,鸟,还有我自己。小沫的样子一直忆不清,画了又擦擦了又画。沉若只在旁边不发一言,手里握着两只盛着清水的杯子,还紧紧依偎在一起。
手里的笔在颤抖,在寒冷,很孤独。因为沉若只是看着,只能看着。
眼里干涩,传来某种熟悉的隐痛,忽地出现那个伤口的影子,不见血也不见光。痛的感觉迅速蔓延,整条神经就这样拉到脑后剧烈跳动。像是在嘲笑,看吧看吧,那里什么都没有,那里早已一片荒芜。揉揉眼睛,紧接着一阵晕眩,空气里的灰尘一下躁动起来。四散交错激烈不停,形成一块梦魇般的阴影压上胸口,窒息难言。画上的面孔笑的一直很忧伤,一股咸腥的液体在喉深处翻涌。忽地喷涌出来,染红了大块大块面积的画布,以小沫的面孔为中心,红色的颜料全是血。
真可惜。
没什么,正好我想不起来那里怎么画。
忘记了?
恩。
或许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瞬间,那面孔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抽离了,扯开一个没有血的伤口。夏远说,有些人有些事情是会一下子突然忘记的,因为那记忆的主人不再想留着它。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头很疼,我要再睡上一下午。
?:?? PM
我梦见了远方的大海。
他的蓝色比天更深沉,也更加孤独。我甚至闻到了海水咸腥苦涩的味道。我看到大群的飞蛾从海中央破茧而出,看上去就像是口中呼出的烟雾。
想起三年前的夏天,夏远执意要走的理由。希望看到海。
又想起海子的诗,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还有,日短夜长,路远马亡。
7:00 PM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对沉若说必须回家了。
倒不是因为这里不好,沉若的父母和我妈一样也经常不在家,只不过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7:20 PM
一路上走走停停,高大林立的楼群像是墓碑停在那里纪念着些什么。
这个城市有着坚硬的令人着迷的外壳,我却总觉得它似是要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我想有一颗硬如磐石的心,让我笑看所有的残败。我害怕流血流汗流泪,我害怕受伤,害怕看到黑暗害怕听到腐烂的声音。
外壳越坚硬的蜗牛,里面的身体就越软弱。
走到一处,灯光亮起,见到路边女孩的背影,有一头亚麻色的短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像以前那样。女孩回头才发现认错了人,其实在那面孔已经忆不起来的时候,错认似乎是逃脱不掉的。
想起王菲的百年孤寂,她唱,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
街道重重叠叠,鹅卵石堆砌的广场上,漂浮着城市惯有的那种喧嚣和躁动。让我难过得想哭泣。
7:30 PM
妈妈不在家,她恐怕是忙得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没关系,我在家里等她。
左眼像是失明了一样,右眼朦朦胧胧一片潮湿的水汽,空气冰凉。浑身打颤回到房间,一入眼又是墙上的那幅油画,色彩已经被时间冲淡了许多。窗外灯火通明,高处的夜空却还是暗淡,浮云顶替飞鸟遮蔽了天空,不见天光。
夏远悄悄在桌上留了字条,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
漠然:
其实不是我忘了,是你忘了,你忘了你知道吗?小沫的每件事我都记得很清楚,你们告别那天,下了大雨,后来我和你妈妈赶到的时候你已经昏迷不醒了。路边的人说车把小沫撞了,拖着走了几十米,死的时候脸都血肉模糊了。你过去追,也被车撞了,昏迷了一个礼拜差点成了植物人。你一醒来就把这些都忘了,我和你妈妈怕你伤心,就说小沫已经安全地走了,你伤心过度生了一周的病。你是不是觉得眼睛深处经常会痛?那是车祸伤了你的神经。今天你忽然问我记不记得小沫,我其实难过的要死。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把她忘了可你现在又问起来了,我其实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当时只能对你说不知道。后来我趁你出门前去上厕所的时候偷偷留了这张字条,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得不告诉你。知道了真相以后就请忘掉她吧,这回忆最好不留。要记住,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选择忘记。
-----------------------------------夏远
头有些晕眼睛又开始痛,记忆如潮水来袭。
那时的天很阴沉,空气里压抑着浮躁炎热的水分子,我们就在楼后面那堵灰色的大砖墙面前告别。墙对面的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我们一起,听见时光断裂的声音。几分钟,大滴大滴的雨点忽然落下来。玩耍的孩子们慌乱的躲进屋檐下,不知所措的望着街上瞬间卷起的汹涌溪流。我对她说,要走了,要好好过,要记得回来看看。忽然就哭了。
漠然,以后我不在了,你不会忘了我吧。
一瞬间强光刺眼,梦魇般的阴影再度压上胸口。夏天的大雨,小沫说的话,黑色的车,小沫的面孔一下变成一片血红色,难以辨认。
喉间鲜血翻涌,再次染红了家中的另一张画布。
10:00 AM
很普通的,我像平时那样约沉若出来。
向她告别。
我要走了,去远方,来跟你告别。
这次换做我来问为什么了。
这所城市有我不愉快的记忆,我打算一个人旅行,然后忘掉这些。
漠然,你真的是一个太过孤独的人,只有孤独的人才会沉迷在时间中无法自拔。
我笑了,冬日下午的阳光恰好从高墙间穿过照在我的嘴角,一抹金黄。
是的。然而你也不能将我解救。不是不会,是不能,哪怕是你也不能。
沉若给了我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莫名地感到切肤之痛。她的长发还在发光,两片嘴唇剧烈颤抖。额头,发线,眉梢,构成美丽忧伤的脸。用手顺过贴在额前的头发,表情就那样显露无疑。眼角下悄悄划过的泪光。
可是,我爱你。虽然这只是个太稀松太平常的字眼。
沉若最终把这话藏在了心底,但她的脸上已经泄露了一切。
最终我还是没有留下来,踏上离开那个城市的火车时我笑了。似乎那一瞬间,由记忆构成的束缚我多年的桎梏已经被我挣开了那样。然后下一秒钟我开始思念沉若,渐渐构成新的不可抑制的痛。火车经过山洞的时候天光消失不见,就像那时的飞鸟穿越时间穿越冬夏遮蔽住我脸上浮现的悲伤,遮蔽住一个又一个的夏天和冬天。
遮蔽你也遮蔽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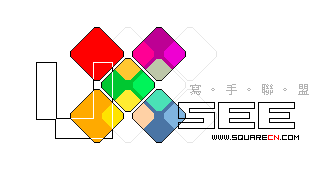
你们面对面站着,站了很久,然后又各自消失在人海了。
没什么。
我对自己说没什么。我是漠然。
6:50 PM
冬天就是会这样,夜晚不断地提前提前再提前,努力地压榨掉白昼的每一丝阳光。黑暗的工作比许多人都要勤奋得多。
就这样,天边的残光模糊地颤抖跳跃,可怜兮兮。
或许是黑夜,把我浇灌成一棵独立生长的倔强植物。手中的空酒杯,在灯光下起舞,说不出是为谁而泣。
三年前的时候小沫走的时候很难过。我们。
是个夏天。我记得那个下午她忽然来到我家找我,说她要走了。那时的天很阴沉,空气里压抑着浮躁炎热的水分子,我们就在楼后面那堵灰色的大砖墙面前告别。墙对面的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我们一起,听见时光断裂的声音。这回忆断了,便再也寻不回来。对此无论是我还是小沫,都明白。但我们也同样都无能为力。
几分钟,大滴大滴的雨点忽然落下来。玩耍的孩子们慌乱的躲进屋檐下,不知所措的望着街上瞬间卷起的汹涌溪流。
我对她说,要走了,要好好过,要记得回来看看。
忽然就哭了。
我明明看见小沫张开了嘴唇,那久远的声音却被大雨和时光湮灭,不能辨认。直到那时的天,那灰色的墙,高大的树在记忆中缓慢褪色,依然辩不清小沫最后对我说的话。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时光流逝,此前做过的一切便无法弥补。我们此后没有再联系。
回忆就这样中断了。
7:00 PM
天黑黑,我不知道,是不是又要下雨。
8:20 PM
妈妈打来电话,和往常一样说食物还是在冰箱里面,今天晚上她还是不会回家。
我很平静听她说完这些,然后挂了电话。若是以前我会发很长时间的呆,掉眼泪,然后问爸呢,爸在哪里呢?现在我不会再那样问了,因为那样很傻,因为那样妈妈也会伤心。我比以前懂事了,只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发很长时间的呆然后安静地掉眼泪,只不过不会吵也不会闹。其实我还是很软弱,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不过是装作很坚强罢了。
想起沉若对我说,漠然,你要知道,外壳越坚硬的蜗牛,里面的身体就越软弱。
我小的时候爸就和另外一个女人走了,留下我和母亲。还好母亲很能干,自从爸走了以后她真得变坚强了,坚强到一个人让我们两人这个破败的家维持着不错的生活。只有我一个人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他走的那个晚上。不知多少年以后我开始告诉自己要坚强,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唯一的支柱。但我能做到的,仅仅只是不在妈妈面前掉眼泪而已。
其实爸长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是迷恋于“父亲”这个称呼。后来的时间里夏远告诉我说,有些人有些事情是会一下子突然忘记的,因为那记忆的主人不再想留着它。再后来的时间里我开始相信这句话。
9:10 PM
桌上随便地堆放了牙膏状的颜料,没有削完的铅笔。未完成的画布还挂在墙上,干涸的厚重油彩,在记忆中等待褪色。
墙上的那幅是在小沫走之后画的,一直没有画完。记忆中小沫给我看过的画面一直都找不全,记得是一片无边的金黄麦田,穿着裙子的女孩在其中奔跑,稻草人在田中安静地守望,身上栖满了乌鸦,天空是一片空旷,浮云在发光。
小沫喜欢画画,于是后来我也喜欢了。
仅此而已。
9:40 PM
对待一件事情,沉迷是致命的。
比如回忆。
我现在时常会想起小沫,想象她现在过得怎样。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我的话,也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最后对她说,要走了,要好好过,要记得回来看看。其实就算她回来过,我也早已经搬了家。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感情,改变回忆,以及改变与之相关的许多事情。纵使了解,我们也对此无能为力。
唯有沉迷。
9:50 PM
我出了门,去买一包烟。
10:00 PM
最后付钱的时候我才发现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杯,沉迷会使人在恍惚中忽略自身现在的状态。这正是它的危险所在。
手机响了,夏远的短信。
放寒假了吧,过年的时候你们一家来东北吧,两个人太冷清了。
好的,我跟妈说去。
我带你去看海。
你说,时间真的能改变一切么?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但它真的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无能为力。别想太多了,漠然,你还是个孩子。
恩我知道了。
夏远是我上初中时的朋友,高大清瘦,笑容干净明亮,大多数时候都很沉默。以前我们经常到各自的家中去玩。家长互相之间也因此熟络了。后来夏远回了东北的老家,我们两家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逢放假过节的时候,我和妈偶尔便去他家。夏远的父母也很热情,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家的人一向是不容易结交到什么朋友的。
夏远和我都长得很高很瘦,我们也同样都很沉默。但与他相比我永远还像个孩子。
0:50 AM
关机睡觉。
8:40 AM
我是被手机的铃声吵醒的。才想起昨天晚上沉若发的短信一直都没有回。
认识沉若的时间不长,可能也就半年的时间,却是很快乐的半年。每天放学我都会送她回家,有时候会用手指捏她的鼻子,拍她的头。她尖叫着追打我。我就抱头假装求饶。然后我便在一旁看着她笑,声音会一直传到街的尽头,放肆而孤单。
有时候会逼问自己究竟把沉若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却问不出个究竟。我们都是这样,带着各自的伤口不肯脱身,而企图内心挣扎的人是孤独的。我们也都是这样在互相温暖着,安慰着。
或者说,我们相爱。
这只是个太稀松太平常的字眼。
9:00 AM
草草洗梳,发呆,看窗外苍白的天空,像白色的洞口。
然后回沉若的短信。
我失神了。
哦没事你总是这样。
出什么事了?
没有。
11:30 AM
中午妈妈回来了。
我说夏远约咱们去东北,妈就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回去睡觉,什么话也没有多说。看得出来她很累。
外壳越坚硬的蜗牛,里面的身体就越软弱。
忽然想起这句话,沉若说的。也不知道她是在说我,或是说自己。
1:00 PM
整点,正午的阳光激烈。鸽子飞过对楼的天台。
1:10 PM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在我的脑海中是一片纯白色的记忆。我和小沫住的两栋楼是对着的,鸽子也是那样飞过各自的窗前。
羽毛落下来,飞鸟歌唱。
飞鸟路过只用了几分钟。
几分钟,一次昏厥。
几分钟,几个生命诞生,几个生命沦丧。
这几分钟在大多数的生命中不值一提。
直到那时的天,那灰色的墙,高大的树在记忆中缓慢褪色。偶尔起床还会看到一对鸟儿在快乐的飞翔,心里就会有最不可言说的熟悉隐痛,低下头让泪水稀薄了颜料。
画布安静地挂在墙上,一张CD反复播放。
1:30 PM
沉若把我约到街边,她说,漠然,我们分手。
那一瞬间飞鸟如同浮云蔽日的在冬天里飞过,穿越时间穿越冬夏也遮蔽了沉若那时的面容。
为什么?
不知道。
还爱我么?
爱。
那我们不要分开,我们没理由分开。
那就可以在一起了吗?
恩。
多久?
我不知道。
天空和日光变得很沉默,城市在那一刻瞬间灰白。指尖冰凉,积雪温暖,掉了漆皮的指示牌有四个方向各奔东西。叶子飞走,树影稀薄,没有人知道何时该分开,飘去何方。被拆除的砖头安静地躺在地上,路过的人也不会多看它一眼,寂寞就忽然来袭。只有冬天一直寡言,用寒冷诉说着孤独和创伤,尘土飞扬。
一场稀薄的幻觉快速播放,然后我听见她说。
好吧。
5:00 PM
夏远告诉我说,他已经回来了,明天来看我。
夏远。这个名字是个魔咒,她和他在三年前的夏天走远。一片炎热潮湿的气息。
眼睛发涩,像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隐痛,来自一个幽深的伤口。
11:00 PM
早早睡觉。明天早上夏远就会来。
7:50 AM
第二天下雪了。
夏远变化不大,还是一样的沉默寡言。他进屋的时候,我一回身看见墙上铺展开的大大的画布,眼里就隐隐的痛。
我问,夏远,你还记得小沫么?
夏远盯着那幅画不发一言,眼里氤氲一层灰蒙蒙的雾气。张口想起说些什么,终又禁闭双唇。窗外一片厚重的银白色,天空苍凉沉默。夏远低下头,颈间一阵冰凉的闪光。粗重的银制项链,坠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像是某种束缚,某种桎梏。
不记得了啊。
夏远走过去抚摩那画布,试图回忆些什么,三年前的夏天同样也是他离开的季节。我开了窗子,几片雪花飘进来,落在画布上就融化了,夏远眼里仍是厚重的大雾。
还记得三年前楼顶天台的飞鸟吗?
夏远忽地停滞,回过头时眼里冰雪散尽雾气消亡,又是曾经的干净明亮。接下来一个微笑。
记得呀,不是我们两个人喂的吗?
那一秒心跳漏过一拍,窗外光芒瞬间绽放忽又黯淡,最终一片灰白色。既然有些人有些事情是会一下子突然忘记的,因为那记忆的主人不再想留着它。那么什么时候我会想到放弃。
11:30 AM
中午饭以前夏远走了,我独自接沉若去吃饭。
我把三年前我们住的地方指给她看,心里一片荒芜。看吧,看吧,什么都没有。沉若冰凉的手覆盖上我的眼,就痛得难以自制,眼睛最深处幽深的伤口暗潮涌动,最终碎成一朵朵模糊的水印。然后眼里大雾弥漫,阳光透过沉若的掌心一片暗红色,暖如地血。手指的方向两座楼孤傲地对立,不见飞鸟,不见夏天的影子。手指寂寞的蜷缩在一起,形成一个可耻姿势。
忘了那些好吗?为我。
树影稀薄,我看见阳光下空气中那些缓慢凝滞的柔软灰尘,心里就躁动不安。我知道决定会影响很多事情,但忘记绝不会说到做到。
最后我只说,让我回家,我想回家。
我很傻,傻到自以为很聪明。
1:30 PM
我晕倒了,现在是在沉若的家里。
我和沉若中间摆着一个桌子,两杯清水,过了正午的阳光开始疲惫。
冬天像一个无限扩大的白色洞口,长的无边无尽,我们被吸入其中无法自拔。路途坎坷有些人散落在了天涯。
我喝了口水。
你说,冬天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傻东西,你随时可以出来。
你会帮我么?
不是不会,是不能。哪怕是我,也不能。
洗手,然后打开窗子。阳光开始与我对峙在窗户的两侧,彼此都那样的沉默。空气很凉但下午光线充足,只是天空的颜色有些苍白和我一样。沉若在背后轻唤我的名字,漠然,于是我回头。隔着雾气看到沉若的长发间隙在发光,就伸手去抚,又想起小沫亚麻色的短发在夏天的阳光下沾上了颜料。
我说,我要画最后一幅画。
好。
2:30 PM
沉若也学过画画,在她家里就可以。
我用铅笔,画了一堵高大的灰色的墙,夏天的树,鸟,还有我自己。小沫的样子一直忆不清,画了又擦擦了又画。沉若只在旁边不发一言,手里握着两只盛着清水的杯子,还紧紧依偎在一起。
手里的笔在颤抖,在寒冷,很孤独。因为沉若只是看着,只能看着。
眼里干涩,传来某种熟悉的隐痛,忽地出现那个伤口的影子,不见血也不见光。痛的感觉迅速蔓延,整条神经就这样拉到脑后剧烈跳动。像是在嘲笑,看吧看吧,那里什么都没有,那里早已一片荒芜。揉揉眼睛,紧接着一阵晕眩,空气里的灰尘一下躁动起来。四散交错激烈不停,形成一块梦魇般的阴影压上胸口,窒息难言。画上的面孔笑的一直很忧伤,一股咸腥的液体在喉深处翻涌。忽地喷涌出来,染红了大块大块面积的画布,以小沫的面孔为中心,红色的颜料全是血。
真可惜。
没什么,正好我想不起来那里怎么画。
忘记了?
恩。
或许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瞬间,那面孔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抽离了,扯开一个没有血的伤口。夏远说,有些人有些事情是会一下子突然忘记的,因为那记忆的主人不再想留着它。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头很疼,我要再睡上一下午。
?:?? PM
我梦见了远方的大海。
他的蓝色比天更深沉,也更加孤独。我甚至闻到了海水咸腥苦涩的味道。我看到大群的飞蛾从海中央破茧而出,看上去就像是口中呼出的烟雾。
想起三年前的夏天,夏远执意要走的理由。希望看到海。
又想起海子的诗,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还有,日短夜长,路远马亡。
7:00 PM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对沉若说必须回家了。
倒不是因为这里不好,沉若的父母和我妈一样也经常不在家,只不过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7:20 PM
一路上走走停停,高大林立的楼群像是墓碑停在那里纪念着些什么。
这个城市有着坚硬的令人着迷的外壳,我却总觉得它似是要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我想有一颗硬如磐石的心,让我笑看所有的残败。我害怕流血流汗流泪,我害怕受伤,害怕看到黑暗害怕听到腐烂的声音。
外壳越坚硬的蜗牛,里面的身体就越软弱。
走到一处,灯光亮起,见到路边女孩的背影,有一头亚麻色的短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像以前那样。女孩回头才发现认错了人,其实在那面孔已经忆不起来的时候,错认似乎是逃脱不掉的。
想起王菲的百年孤寂,她唱,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
街道重重叠叠,鹅卵石堆砌的广场上,漂浮着城市惯有的那种喧嚣和躁动。让我难过得想哭泣。
7:30 PM
妈妈不在家,她恐怕是忙得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没关系,我在家里等她。
左眼像是失明了一样,右眼朦朦胧胧一片潮湿的水汽,空气冰凉。浑身打颤回到房间,一入眼又是墙上的那幅油画,色彩已经被时间冲淡了许多。窗外灯火通明,高处的夜空却还是暗淡,浮云顶替飞鸟遮蔽了天空,不见天光。
夏远悄悄在桌上留了字条,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
漠然:
其实不是我忘了,是你忘了,你忘了你知道吗?小沫的每件事我都记得很清楚,你们告别那天,下了大雨,后来我和你妈妈赶到的时候你已经昏迷不醒了。路边的人说车把小沫撞了,拖着走了几十米,死的时候脸都血肉模糊了。你过去追,也被车撞了,昏迷了一个礼拜差点成了植物人。你一醒来就把这些都忘了,我和你妈妈怕你伤心,就说小沫已经安全地走了,你伤心过度生了一周的病。你是不是觉得眼睛深处经常会痛?那是车祸伤了你的神经。今天你忽然问我记不记得小沫,我其实难过的要死。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把她忘了可你现在又问起来了,我其实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当时只能对你说不知道。后来我趁你出门前去上厕所的时候偷偷留了这张字条,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得不告诉你。知道了真相以后就请忘掉她吧,这回忆最好不留。要记住,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选择忘记。
-----------------------------------夏远
头有些晕眼睛又开始痛,记忆如潮水来袭。
那时的天很阴沉,空气里压抑着浮躁炎热的水分子,我们就在楼后面那堵灰色的大砖墙面前告别。墙对面的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我们一起,听见时光断裂的声音。几分钟,大滴大滴的雨点忽然落下来。玩耍的孩子们慌乱的躲进屋檐下,不知所措的望着街上瞬间卷起的汹涌溪流。我对她说,要走了,要好好过,要记得回来看看。忽然就哭了。
漠然,以后我不在了,你不会忘了我吧。
一瞬间强光刺眼,梦魇般的阴影再度压上胸口。夏天的大雨,小沫说的话,黑色的车,小沫的面孔一下变成一片血红色,难以辨认。
喉间鲜血翻涌,再次染红了家中的另一张画布。
10:00 AM
很普通的,我像平时那样约沉若出来。
向她告别。
我要走了,去远方,来跟你告别。
这次换做我来问为什么了。
这所城市有我不愉快的记忆,我打算一个人旅行,然后忘掉这些。
漠然,你真的是一个太过孤独的人,只有孤独的人才会沉迷在时间中无法自拔。
我笑了,冬日下午的阳光恰好从高墙间穿过照在我的嘴角,一抹金黄。
是的。然而你也不能将我解救。不是不会,是不能,哪怕是你也不能。
沉若给了我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莫名地感到切肤之痛。她的长发还在发光,两片嘴唇剧烈颤抖。额头,发线,眉梢,构成美丽忧伤的脸。用手顺过贴在额前的头发,表情就那样显露无疑。眼角下悄悄划过的泪光。
可是,我爱你。虽然这只是个太稀松太平常的字眼。
沉若最终把这话藏在了心底,但她的脸上已经泄露了一切。
最终我还是没有留下来,踏上离开那个城市的火车时我笑了。似乎那一瞬间,由记忆构成的束缚我多年的桎梏已经被我挣开了那样。然后下一秒钟我开始思念沉若,渐渐构成新的不可抑制的痛。火车经过山洞的时候天光消失不见,就像那时的飞鸟穿越时间穿越冬夏遮蔽住我脸上浮现的悲伤,遮蔽住一个又一个的夏天和冬天。
遮蔽你也遮蔽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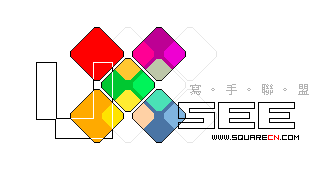
你们面对面站着,站了很久,然后又各自消失在人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