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魔法师(四)
2005-11-19 23:56 | 噩梦
一连几天有着难堪的沉默,却总不知道错在何处。昨天晚上她对我说,以后你别说要给我打电话。于是我明白,说不出话的时候就不要张嘴,不然喉咙会变得沙哑和疼痛。
跟HY提起成长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我说长大就是有一天会张大了嘴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好象一把卡壳的枪,长大了就是在某天以后闭紧嘴巴什么都不说,好象一把锈死的锁。
一直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以前却不总是这样。倾诉的欲望和语言的匮乏,合在一起会变成一种述说不明的痛感。如果说寂寞是文字生存的土壤,文字却让寂寞肆意在蔓延。
于是只剩下,稀薄的幻觉,别人和别人的传说。
七
老去的精灵会扎起长长的马尾,收拾行囊离开那座魔法兴建的大城,当他们身处他乡听到遥远的祷告声时,思念就像盛开的白花。
魔法师从不束头发,左左不忍去探究这背后的真相,因为他已经在老去了。左左仔细观察着魔法师的发色,从白色,到幽蓝,直至出现了一丝黯淡的灰,就像他潮湿的双眼。有时也会映上一层暗红,那是因为太阳是红色的。漫天的风沙融入了人们的血脉,遮天蔽日地吹着,两个月后已找不到白雪的影子。魔法师的眼神疼痛而隐忍,就像在狂风中倔强矗立到最后的灯塔,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如此勉强,只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坚持。
刮风的时候魔法师咳嗽得很厉害,血红的日光慢慢爬上他的脸,消瘦且轮廓分明。左左总能清楚地看见生命的流逝,魔法师一咳嗽她就去倒水,可那水也是掺了沙子的,他从来不喝。就这样一天一天干枯下去,仍记得他答应过左左,他要教她魔法。魔法师的法力也在一天一天的衰退,不再能维持小村庄美丽的梦。有天他一连念了三个咒语,想竖起一道遮挡风沙的屏障,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他细长干枯的手指尴尬地停在空气当中,像一个忘记该做出何样表情的演员。
魔法师在屋里休息,左左忽然想给他讲哥哥的故事,她相信他们是认识的。当左左说到哥哥以前因为偷别人家的水而被十几个人追着在街上跑时,魔法师腼腆地笑笑,手里握着一杯沉淀了红沙的清水,折射出微弱的光芒。或许他想到自己在那座大城里的童年,或许他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喜欢冒险的同族,但他的笑容再也撑不起眼神的黯淡。
在精灵的世界里,黑色是最年轻的颜色,每个刚出生的精灵都有着纯黑色的眼睛。他们的年龄也只能从眼睛的颜色去判断,因为精灵自生至死都是那样的美丽。许多个人类难以想象的时间单位之后,魔法师的眼睛早已被岁月蒙上了潮湿的灰。
于是后来魔法师的法力越来越弱,什么也做不了了,他只能在一边看着左左继续孤独地练习着咒语,偶尔给她一些指导。左左还是那样坚定地努力着,每天晚上跟小狗汇报她的成果。她总是孜孜不倦地说,小狗轻柔地舔着她的手指,直到有一天咬住不放,她才发现她已经太久忘了喂它。她还是从未问过魔法师从哪里来,是不是要接她走,她相信这些都是不用说的。只要她准备好了,就可以飞走,魔法师什么都知道,一切只是在等待她准备好。
那些窗外呼啸的风沙,重新开始盘旋的乌鸦和秃鹰,也都只是,都只是对她的磨难而已。
对话有时候是痛苦的,却有寂寞得想倾诉的欲望,将人压抑到窒息。昨天晚上在左臂上留下了新的刀痕和烟疤,还是没能划得很深很深,因为裸露在外的手臂一直在失温。很久不试,竟然很疼。舔拭伤口的时候,嘴角挂着鲜红的血迹,感到自己是一只丧心病狂的小兽,说不清楚为什么,却总要伤人自伤。我也只能,用长袖遮住阴霾,用笑容掩饰苍白。
还是独自编织琐碎的梦幻,随意写着,痴迷于描写漫天的红沙和寂寞的大城。痴迷于城头瘦长的影子,内心白色的虚空。
八
魔法师在午夜的房间里,谨慎地使用着他所剩无几的法力,想看看远方的月亮,是不是也与这里一样。
左左对魔法师的印象停留在他带她飞行的那一天,那天的魔法师仿佛一张手就能带来这个世界上最为盛大的烟火和幻觉。而现在,那个使用魔法的精灵静静地躺在干草铺成的床上,一言不发。左左坐在他的身旁,继续听他讲着远方的故事。她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久远回忆被时间磨损所受到的痛楚,就像是在幻觉里慢慢消失的魔法。在这个永远干旱的地方,时间是一塑静默的雕像,狂风夹杂红沙呼啸着对它顶礼膜拜,笑看一切灰飞烟灭。
魔法师抬头看天,寻找他家乡那个巨大的带着思念的白洞,却什么都没能找到。他叹了口气,依然是好看的白色,左左把手放过去时,却有风沙吹过的痛感,不再是七彩色的细小泡沫。魔法师苦笑着说法力还是消失了,左左心里明白这是他生命损耗的讯号,却无能为力,只能念几个咒语缓解他因干渴而受到的痛楚。他教她的那些小东西,始终还是没有逆转时间的魔力。
失去法力的魔法师还在继续讲,远方的城堡和美丽的精灵。一切的一切消失以后,只有故事还在继续,孤独地抵抗着时间的魔力。许多许多年以后小村庄会埋在沙土下面,大城也终会破灭,只有传说中的精灵依旧一尘不染。
他说,在城堡的外面,有一个独自生活在小屋里的精灵。她的眼睛是午夜幽深的蓝色,脖子上有蝴蝶型的胎记,呼吸的时候,两块凛冽的锁骨暴露在空气中发出断裂的声响。即使对于那座城堡里面的同族而言,她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存在。据说她会在午夜用魔法炼制使人失忆的药水,然后望着城堡方向盛大的烟火哭泣。没有人知道她是否真的炼出了那样的药水,也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哭泣,她自始至终住在那里独守沉默,丧失了所有的过去和未来。还有人说她掌管着这座城堡里所有精灵的梦境,在午夜给他们带去美好的幻觉,却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在那间小房里,她的寂寞使时间停摆。
魔法师到最后也不知道那个精灵有着怎样的过去,因为她说连她自己也忘记了。他点点头坚定不移,那穿越千年的疼痛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空洞,怎样填补也还是难以追回。以至于在她死后,他也总要到那小屋里去坐坐,看看陪伴她千年的究竟是怎样的寂寞。
那时他还年轻,是个有着纯黑色眼睛的高大精灵,喜欢在每天的清晨到城门外晒温暖的阳光,直到每一丝头发都染上好看的金色。他走进那间房的时候,阳光就在他的背后铺洒了一地,是比烟火更加美丽的颜色,瞬间击破了那间房里积累千年的沉默。隐居的精灵错愕地转身,眼角有碎乱的纹路,被时间磨损的痕迹,却依然美丽。手里握着半张纸片,写着失传的咒语,崭新的一段岁月在阳光下悄悄开启。
很多年以后,隐居的精灵离开了她的小屋,去做一生最后一次的旅行。她总要想起那个早晨的阳光,有着穿越时间的力量。在那之前,她以为多年的寂寞早已将她摧毁,使她忘记如何倾诉如何与人对话,只能在幻觉中永远永远沉堕下去。很多年以后,她独自行走在世界各地,学会与人相处,也学会在半张纸片上写一些咒语以外的东西。
那些信件要穿过很长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城堡,但他总记得每天早晨去城头张望是否有远方来的信使,因为这已是他和她唯一的联系。有时他也会写一些回信给她,却不知道该寄向哪里。
他曾执意要和她一起走,因为他知道,一直隐居的她其实最害怕孤独。她却只是笑笑,让他帮自己束头发,扎起长长的马尾,然后在一个冬天迟到的早晨里不辞而别。
她不愿带他一起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还有太长的寿命要过,长得让苍老的她已无法再陪下去了。于是,被留下的魔法师只有每天守在城头眺望远方,默默地思念,静静地让时间改变他眼睛的颜色。不知过了多少年,终于,他也老了,于是他去那间空置的小屋里坐了很久,然后起身离开,去完成他最后一次的旅行。
她走后很多年,在魔法师也要离开那座城堡的时候,他倔强地拒绝将头发束起,因为她说过,他一辈子只可以为她一个人,扎马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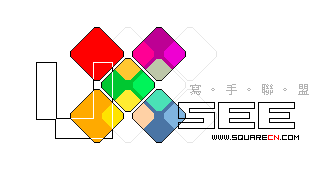
我还只是个孩子.如果我做了什么,我希望你能知道.关于我的小小绝望,和17岁的眉飞色舞.
跟HY提起成长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我说长大就是有一天会张大了嘴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好象一把卡壳的枪,长大了就是在某天以后闭紧嘴巴什么都不说,好象一把锈死的锁。
一直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以前却不总是这样。倾诉的欲望和语言的匮乏,合在一起会变成一种述说不明的痛感。如果说寂寞是文字生存的土壤,文字却让寂寞肆意在蔓延。
于是只剩下,稀薄的幻觉,别人和别人的传说。
七
老去的精灵会扎起长长的马尾,收拾行囊离开那座魔法兴建的大城,当他们身处他乡听到遥远的祷告声时,思念就像盛开的白花。
魔法师从不束头发,左左不忍去探究这背后的真相,因为他已经在老去了。左左仔细观察着魔法师的发色,从白色,到幽蓝,直至出现了一丝黯淡的灰,就像他潮湿的双眼。有时也会映上一层暗红,那是因为太阳是红色的。漫天的风沙融入了人们的血脉,遮天蔽日地吹着,两个月后已找不到白雪的影子。魔法师的眼神疼痛而隐忍,就像在狂风中倔强矗立到最后的灯塔,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如此勉强,只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坚持。
刮风的时候魔法师咳嗽得很厉害,血红的日光慢慢爬上他的脸,消瘦且轮廓分明。左左总能清楚地看见生命的流逝,魔法师一咳嗽她就去倒水,可那水也是掺了沙子的,他从来不喝。就这样一天一天干枯下去,仍记得他答应过左左,他要教她魔法。魔法师的法力也在一天一天的衰退,不再能维持小村庄美丽的梦。有天他一连念了三个咒语,想竖起一道遮挡风沙的屏障,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他细长干枯的手指尴尬地停在空气当中,像一个忘记该做出何样表情的演员。
魔法师在屋里休息,左左忽然想给他讲哥哥的故事,她相信他们是认识的。当左左说到哥哥以前因为偷别人家的水而被十几个人追着在街上跑时,魔法师腼腆地笑笑,手里握着一杯沉淀了红沙的清水,折射出微弱的光芒。或许他想到自己在那座大城里的童年,或许他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喜欢冒险的同族,但他的笑容再也撑不起眼神的黯淡。
在精灵的世界里,黑色是最年轻的颜色,每个刚出生的精灵都有着纯黑色的眼睛。他们的年龄也只能从眼睛的颜色去判断,因为精灵自生至死都是那样的美丽。许多个人类难以想象的时间单位之后,魔法师的眼睛早已被岁月蒙上了潮湿的灰。
于是后来魔法师的法力越来越弱,什么也做不了了,他只能在一边看着左左继续孤独地练习着咒语,偶尔给她一些指导。左左还是那样坚定地努力着,每天晚上跟小狗汇报她的成果。她总是孜孜不倦地说,小狗轻柔地舔着她的手指,直到有一天咬住不放,她才发现她已经太久忘了喂它。她还是从未问过魔法师从哪里来,是不是要接她走,她相信这些都是不用说的。只要她准备好了,就可以飞走,魔法师什么都知道,一切只是在等待她准备好。
那些窗外呼啸的风沙,重新开始盘旋的乌鸦和秃鹰,也都只是,都只是对她的磨难而已。
对话有时候是痛苦的,却有寂寞得想倾诉的欲望,将人压抑到窒息。昨天晚上在左臂上留下了新的刀痕和烟疤,还是没能划得很深很深,因为裸露在外的手臂一直在失温。很久不试,竟然很疼。舔拭伤口的时候,嘴角挂着鲜红的血迹,感到自己是一只丧心病狂的小兽,说不清楚为什么,却总要伤人自伤。我也只能,用长袖遮住阴霾,用笑容掩饰苍白。
还是独自编织琐碎的梦幻,随意写着,痴迷于描写漫天的红沙和寂寞的大城。痴迷于城头瘦长的影子,内心白色的虚空。
八
魔法师在午夜的房间里,谨慎地使用着他所剩无几的法力,想看看远方的月亮,是不是也与这里一样。
左左对魔法师的印象停留在他带她飞行的那一天,那天的魔法师仿佛一张手就能带来这个世界上最为盛大的烟火和幻觉。而现在,那个使用魔法的精灵静静地躺在干草铺成的床上,一言不发。左左坐在他的身旁,继续听他讲着远方的故事。她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久远回忆被时间磨损所受到的痛楚,就像是在幻觉里慢慢消失的魔法。在这个永远干旱的地方,时间是一塑静默的雕像,狂风夹杂红沙呼啸着对它顶礼膜拜,笑看一切灰飞烟灭。
魔法师抬头看天,寻找他家乡那个巨大的带着思念的白洞,却什么都没能找到。他叹了口气,依然是好看的白色,左左把手放过去时,却有风沙吹过的痛感,不再是七彩色的细小泡沫。魔法师苦笑着说法力还是消失了,左左心里明白这是他生命损耗的讯号,却无能为力,只能念几个咒语缓解他因干渴而受到的痛楚。他教她的那些小东西,始终还是没有逆转时间的魔力。
失去法力的魔法师还在继续讲,远方的城堡和美丽的精灵。一切的一切消失以后,只有故事还在继续,孤独地抵抗着时间的魔力。许多许多年以后小村庄会埋在沙土下面,大城也终会破灭,只有传说中的精灵依旧一尘不染。
他说,在城堡的外面,有一个独自生活在小屋里的精灵。她的眼睛是午夜幽深的蓝色,脖子上有蝴蝶型的胎记,呼吸的时候,两块凛冽的锁骨暴露在空气中发出断裂的声响。即使对于那座城堡里面的同族而言,她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存在。据说她会在午夜用魔法炼制使人失忆的药水,然后望着城堡方向盛大的烟火哭泣。没有人知道她是否真的炼出了那样的药水,也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哭泣,她自始至终住在那里独守沉默,丧失了所有的过去和未来。还有人说她掌管着这座城堡里所有精灵的梦境,在午夜给他们带去美好的幻觉,却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在那间小房里,她的寂寞使时间停摆。
魔法师到最后也不知道那个精灵有着怎样的过去,因为她说连她自己也忘记了。他点点头坚定不移,那穿越千年的疼痛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空洞,怎样填补也还是难以追回。以至于在她死后,他也总要到那小屋里去坐坐,看看陪伴她千年的究竟是怎样的寂寞。
那时他还年轻,是个有着纯黑色眼睛的高大精灵,喜欢在每天的清晨到城门外晒温暖的阳光,直到每一丝头发都染上好看的金色。他走进那间房的时候,阳光就在他的背后铺洒了一地,是比烟火更加美丽的颜色,瞬间击破了那间房里积累千年的沉默。隐居的精灵错愕地转身,眼角有碎乱的纹路,被时间磨损的痕迹,却依然美丽。手里握着半张纸片,写着失传的咒语,崭新的一段岁月在阳光下悄悄开启。
很多年以后,隐居的精灵离开了她的小屋,去做一生最后一次的旅行。她总要想起那个早晨的阳光,有着穿越时间的力量。在那之前,她以为多年的寂寞早已将她摧毁,使她忘记如何倾诉如何与人对话,只能在幻觉中永远永远沉堕下去。很多年以后,她独自行走在世界各地,学会与人相处,也学会在半张纸片上写一些咒语以外的东西。
那些信件要穿过很长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城堡,但他总记得每天早晨去城头张望是否有远方来的信使,因为这已是他和她唯一的联系。有时他也会写一些回信给她,却不知道该寄向哪里。
他曾执意要和她一起走,因为他知道,一直隐居的她其实最害怕孤独。她却只是笑笑,让他帮自己束头发,扎起长长的马尾,然后在一个冬天迟到的早晨里不辞而别。
她不愿带他一起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还有太长的寿命要过,长得让苍老的她已无法再陪下去了。于是,被留下的魔法师只有每天守在城头眺望远方,默默地思念,静静地让时间改变他眼睛的颜色。不知过了多少年,终于,他也老了,于是他去那间空置的小屋里坐了很久,然后起身离开,去完成他最后一次的旅行。
她走后很多年,在魔法师也要离开那座城堡的时候,他倔强地拒绝将头发束起,因为她说过,他一辈子只可以为她一个人,扎马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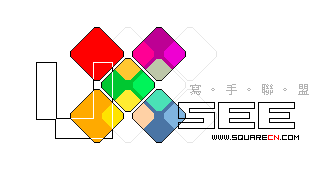
我还只是个孩子.如果我做了什么,我希望你能知道.关于我的小小绝望,和17岁的眉飞色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