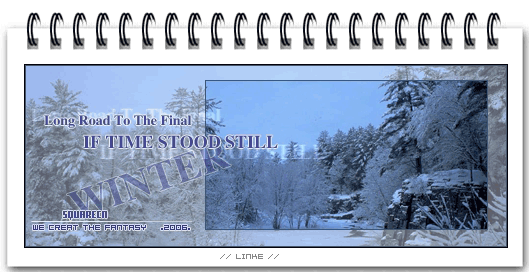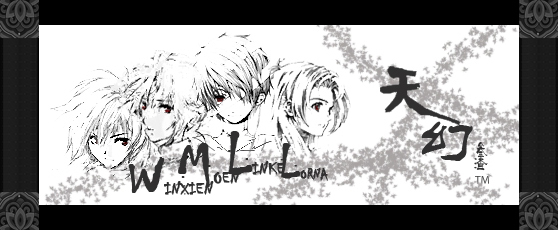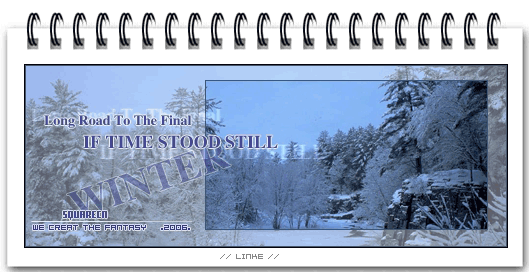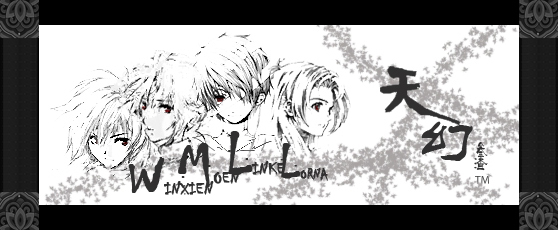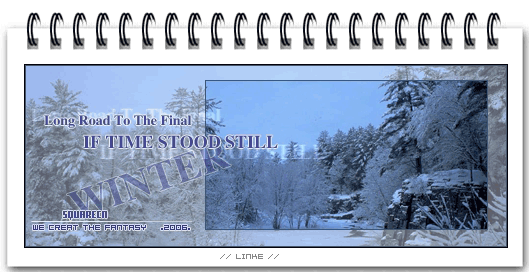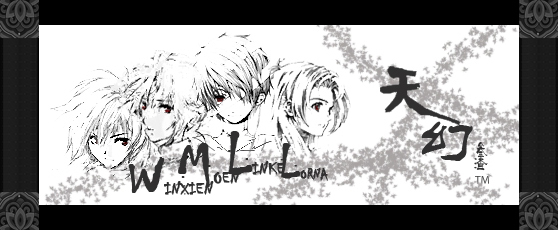不二...
2006-01-14 03:58 | 林柯
| 不二
| 不二•无望
每年有两个人得这种病,没想到其中一个会是我。
当时在刷牙,正对着洗脸池上方的镜子呲牙咧嘴地吐着白泡沫,然后看着里面的自己,仔细地看,除了水平翻转以外,还有了什么不同吧,却又描绘不出,是眼睛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多半是脊柱扭曲了,放水洗脸,凑过去看镜子,接着突然感到眩晕,模糊,镜子,里面的东西,周遭一切,模糊,继而黑过去…
醒来搞不清地点,先是白晃晃的日光灯灯光刺过来,白的刺眼和黑的吞食,说起来最终效果是一样的,都是盲目。我抬手挡着,扭头看到小军站在一旁把脸凑了过来说“你醒了”,我挣扎坐起来,发现是医院,他说当时我伏在洗脸池上,脸埋进盛满水的池子里。
“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的肺就成暖水袋了…”他耸肩道。
这时候走进来一个医生,问我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好,我摸着脸说我就发觉这眼睛不在一条线上,他听了笑,说那倒是小事,伸手接过身后护士手中的资料袋,抽出胸片说其他都还好,我要过来,看着上面白色诡异的一条一条,要是人都是骨头架子,没了皮肉内脏,这,大概以后碰到我有人会说“哎呀你的左边眼洞比右边眼洞大呢”,或者“我觉得你的尾椎真的好有型”这样。
小事?是的,同样的事情,对某些人来说,至关重要,而对另外的一些人,毫无意义。
想莫名其妙的这些可能太过专注,医生以为我有什么包袱,想开导我,却又无从下手,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对他说有什么照直说吧反正我是没家属给你叫进办公室的。
医生就两种情况下爽快,一个是你得了病随便就能治好的时候,他给你说你病得忒严重不治麻烦大了,然后开一些疗效猛价钱更猛的药给你;另一个是你得了病什么药都治不好的时候,他说你其实根本没啥要紧就是肝腹水把水抽了就行了,然后下来问谁是他家属来办公室一趟,说他想吃什么给吃什么,反正就这一个礼拜了。
他轻轻地笑然后告诉我说我确实得了病,每年特定时候就有两个人得的病。
“你这情况,叫‘无望’,第一个得这病症的患者自己取的名字…”然后我问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大概就是对什么都没有希望,或者说对什么都不抱想法,没有期望。末了他说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医治的方法,但是建议我先找找心理医生试试,他告诉我他姓马,会尽力帮助我。
等他走了我立马穿鞋下床,刚在一旁听得满面愁容的小军惊呼说你上哪。
“回去,他不是说我没期望么,我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离开这鬼地方…”我走到病房门口转身说,看他表情跟见了妖精似的。
什么什么无望,什么什么左手手背有一扇形标记,什么什么会间隙性昏迷因为脑部供血不足,都是狗屁。坐在车上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左手手背上暗红色的一扇形,小军把位子让给我,站我旁边,一手拉着吊环一边低头地问我说“你真没事吧”,我不耐烦地抬头笑着,伸手在他面前比划:“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还活得屁颠屁颠的?少听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呢,这个就是静脉而已,现在欲望多了去了,想吃猪蹄想喝雪碧想睡觉还有原始生理冲动行不行?”他听了没说话,愣愣地盯了我一会,然后转头望着窗外,轻声说你没事才怪,我撇撇嘴又要发话,瞟到身边坐的一大娘听了我刚才说的那些脸色都紫了,才收住话头,继续埋头发愣。
不知是不是白天睡得太多,晚上我竟然睡不着了,躺床上努力地回忆有没有什么是得这个病的诱因,却怎么也找不到线索,关于过去的记忆被模糊,理不清楚。像是莫名其妙的被划去了一笔,断掉了。我从被窝里拿出手借着宿舍外的昏暗灯光仔细地看着,那块扇形静静地匍匐在我的手背上。那些本是一体,本是很久以前自己埋下的什么,然后在今时今日滋长起来,我却无从知晓它的来源,以及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闭上眼把手背放在嘴唇上,没有异样,或许也正是此前这样地认定,才会疏忽从而引发现在的情况,没有缺点本身就是一个缺点。都是些自以为是。
想起早上晕倒前最后一幕,镜子里那个自己,看不清楚。
我是谁……
| 不二•雪凌
第二天中午放学的时候一个人走出教学楼,听到背后有人叫我的名字,转头看是班上的一女生,叫什么雪凌,方雪凌?大概,班上的人我有一半不知道名字,还有一半的一半知道名字却又和本人对不上号,所以说对于自己没有什么影响的人,不用在意,名字毫无意义。
“班上的文艺委员,方雪凌。”笑着自我介绍。
“嗯…”
“病就好了?没事?”
“没有。”怎么又来一个?
“哦,昨天上课你没到辅导员来说的…怎么样?一起吃午饭吧。”还是笑,精神得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吃午饭的?”终于不笑了。
“吃,不过怎么找我?”
“恩哼,作为班上的文艺委员关心同学是理所当…呵呵看来跟这个没关系哈。”又笑,还耸肩扮鬼脸。
我撇嘴不理,转身要走,她又“哎哎”地叫住我,绕到我前面:“是真的有事找你哎你这人真是…”
“什么事究竟…”我皱眉头。
“看这个,明白了吧。”她抬手。
“嗯,明白了,淡粉色指甲盖。”
“喂喂谁让你看这个的,这里…”
“……”
“吃什么?或者该问有什么不吃?”她低头翻着菜单。
“随便,重点不在这里。”拥挤的饭馆,风扇吹的发狂还是热的不行,我隔着玻璃望着外面刺眼的阳光。
“那重点在哪里,嗯?”她像是故意在套我的话,抬头笑眯眯地对着我,我转头回瞪,她撇嘴挥挥手,“好啦好啦,还说你这病没期望呢,这不是很有想‘了解’的期望么。”
她说的对,对于什么我是下意识想知道的,什么是该去了解而又没了解的,我自己并没有定性,一切顺理成章。她写了菜单交给服务员,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表情淡然地望着窗外。
“喂——”拖长声音叫她。
“嗯?什么事?”转头发愣,简直像忘得一干二净。
“是你说找我有事!”
“哦,是,不过还在犹豫没看出来么…”
“你想什么不说的话我怎么知道……”我调整了下气息,“好吧…你手背上那个…怎么的?
“手背?这个?”她抬手在我眼前晃晃,然后收回去自己看着,右手抚着左手手背上暗红的扇形,“不跟你一样么…嗯,是不是不熟悉的人,不了解的话,不说话就难以沟通?”
“……那当然。”
“那么说,说了就能了解?了解就意味着没伤害了么?”表情竟有点变。
“……”
“呵呵,你吓到了。”她突然指着我捂嘴笑起来,然后又是挥挥手,“没什么的,问着玩,不过我想有些沟通是不需要语言的,真正要沟通不在乎语言,不能沟通有语言也是表面功夫…好了好了,咱们说正题…”
“嗯…”
“…你的话真少哎…”
“正,题…”
“好好好,sorry,对于这个病症你了解多少?”
“无望,手背上有这个,会晕倒,每年两个。”
“就这些?”
“就这些,嗯还有貌似没法医。”
“嗯,准确的说是不知道怎么医,开先心理医生是有介入的,但是如果本人没有想要好起来的期望,那就很棘手……对于无望,你怎么看?”
“没感觉…似乎我并没有出现什么情况。”我想了想回答。
“也可能问题就在这里…”她竟然想的和我一样,“可能是你自以为还是没什么的,但是某个地方其实已经有了缺口,但是……怎么说呢,不太明显,或者你不能发觉,正是无望的一种表现,对什么都木讷吧。”
“嗯…”我随口应到,想了想,却理不出什么头绪,这些问题似乎得拿时间重新思考,才能有新的认知,然而对于这些我第一反应却是……我疑惑地看着她,“…如果照你那么说…你不像是得了这病的人……”
“哦?怎么说?”她笑。
“不是木讷的…”
“是吗?哈哈,谢谢。”她并没有正面回答,菜送上来,她盛了饭递给我,等我再想要弄明白,她已经夹着菜吃起来,我只得作罢,但没一会她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扒了口饭然后看着我,轻声说“只要记到,终会明了”……
后来几乎没再说话,吃完她向我要了手机号说再联系,起身结帐时她一个趔趄,一下捂住鼻子,我一看手指间浸出血来。
“怎么了?”
“没…”她扯了桌上的餐巾纸捂住,“不好意思,你有钱么…”
“有……你那个…”
“那你付下,天热上火而已,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声音变调地说完然后捂着鼻子跑了出去,剩我站那里傻子一样。
怎么我尽认识些这样的家伙?
| 不二•冻云
回到寝室小军说刚才我妈找我,我没回来,等会儿打来。正说着电话就响了。我接起来,一来就问我有什么要紧没有,说是她知道了。我转头盯小军,肯定是他刚才说的,他无所谓地看着我,我说没什么,电话那头她说爸死了…
“儿子,你能不能回来?”苍白的声音,相当苍白。
“说了不想回去…”
“但是你爸都…”
“管我什么事…他说过不认我…”
“你怎么能这样,你爸死前还念叨你,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她开始哭,哭得心烦。
“说了不回去了,你看着办…”
我挂了电话,盯着小军,他也面无表情的盯着我。
“你给说的?”
“那又怎样?”
“多管闲事啊你。”
他还是那么看着我,然后冷笑一声转身回座位上坐下,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玩着,我见他冷战,也坐回自己的桌子前,他突然丢下火机站起来指着我,声音平静得很,还笑:“你他妈就一畜生,我说!”
“有病啊你?”我转头冷眼相对。
“我操,你有病还是我有?你看你他妈的都成什么样了?!老子跟你十几年的交情,现在又成什么样了!”他慢慢说完,甩门走人,寝室安静下来,我耸耸肩,打开电脑准备照例写点什么,看到小军的电脑还开着,桌面,高中的照片,一群男生笑得七仰八叉的,其中有我和他,我俩打学前班就一班,算算大概十七年了,无话不谈的人,现在……像他说的,成什么样了?
什么成什么样,我怎么知道?我没好气地准备写文,一坐半小时,到手机响楞是一个字都没憋出来,我一看号码是陌生的,没接,结果一直响个不停。
“喂!”
“…真厉害,谁惹你了么?”方雪凌。
“干什么?”我收住脾气,闭上眼睛慵懒地回答。
“不干什么,给你号码而已……刚才不好意思了。”
“流鼻血就流鼻血,你跑什么啊?”
“…怕丢丑嘛行不行,我说,下午没课,有空?”
“没有。”
“真干脆,那有什么事?”
“没有…”
“…你这在搞笑吧,下午出来聊聊。”
“没什么好聊的…”
“是么,那关于这病的呢?嗯?”
“你才在搞笑吧,别拐弯抹角的,有话快说啦,正题。”
“…你一直是这样说话的么?”
“正,题。”
“你正面回答下行不行?”
“不关你事,你不说我挂了。”
“……”
没答话,我挂掉,这两天,没病都得整出病来,说不认我的那老头子,罗嗦的妈,不知哪根筋不对的小军,还加上个莫名其妙的丫头。
我看着手背上暗红的印记。我有病?我疯了?还是世界疯了?
| 不二 • 竹尘
又呆坐了一会儿,还是不行,闷热,偶尔有车子呻吟着开过去,另外就是不住的知了乱叫,机箱里风扇已经转到抽筋了,除此再无其他声响,我开始莫名烦躁起来,头开始晕,不知是不是所谓的脑部供血不足。
我关了显示器拿上钱包准备出去买点什么来喝,街上没几个人,地面冒着热气,走到小卖铺指着雪碧正要一听,从里面走出方雪凌,惊喜地“嘿”了我一下,我给嘿懵了。
“被我逮着了吧…”坏坏地笑。
“买水喝也要报告么…你怎么在这里?”
“没,想打个电话而已。”她指指身后小卖铺里面的IP电话。
“哦…”
“好了好了,既然碰到了就去水吧好了,走走走。”不由分说地拉了我就走,回头对一旁老板娘笑着做了“拜拜”的手势。
老板娘拿着冰冷浸手的雪碧在一旁笑的那叫一个酣畅,生意被这丫头给抢了还猛点头:“慢走啊雪凌,男朋友啊…”
我一听差点喷,还想回头申辩,却被方雪凌不耐烦地拉着往前走。
进了水吧坐定,她说刚才午饭我请的,现在她来,我要了冰水。
“刚刚不雪碧么?”掏着钱包发愣。
“除开雪碧就这个,其他的不要。”
“刚刚打电话很大火气哎,没事?”
“…没有,现在好了…鼻子如何?”
“呵呵,也没什么了。”她摸着鼻子笑,“那个…这个病,马医生还说了什么没有?”
“马医生?那个有点高的中年男?”
“嗯…”
“没有了。”
“没有?好吧,我来说,这个病症大概是21年前开始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第43个和第44个……那什么,你今年多大?”
“22。”
“……几月?”
“10。”
“天枰?…几号?”
“你调查户口?”
“好啦说说。”
“5。”
“……”
“咋了?”
“…呃…我也是…”
“……”
“得得,巧合的飞沙走石。我说你…名字好拗口,就叫你‘木木’好不好?”
“随便,反正名字也只是代号。”
“嗯,是,可是重要的人名字就不再是代号而已,因为有感情在里面。”
“你这在写文章么?搞得那么煽情。”
“呵呵,有写,大多是日记。你?”
“也写,不过多数是故事。”
“哦…没这样找人说过话,感觉真不错。”她摇头晃脑笑着说,喝着递上来的果汁。
“找?”我停止喝水放下杯子疑惑地盯着她,“和人说话还要用找的?”
“你看看,你这不又是有想知道的期望么?”又是坏笑。我不耐烦地转头不理。她赶紧伸手在我面前晃,“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要生气吖。”我无动于衷,她收回手一个人发愣,“又是这样,是不是我做人总有问题?所以搞得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转头看,她一脸郁闷相,我摇摇头说:“既然知道有问题,不能改?”
“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当真一个朋友都没有?”她这性格没朋友简直是天方夜谈。
“嗯……”
“是不是只是你单方面这样认为?”
“单方面么?单方面的话是我单方面的认为谁谁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对方却不这样想,曾经连续被两个女生指着说‘认识你这样的人真是倒了霉了’。有时在想,是不是我太过于在乎,所以变成这样……就是说,我对于感情什么的,太在乎,小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可以用尽所有的感情去对一个自认为是很好的、可以真正作为好朋友的人,对她好,或者其他什么,所以别人没我预期想的那样,没有得到想要的回报,就会伤心,其实现在想来所谓的回报也只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已,就算是孩子间的认定也是好的,比如“方雪凌和我是好朋友”,后来知道是一厢情愿,别人并不把我当回事,该学乖了吧,但却改不掉,有时候很坚定,认为只要自己没什么对不起对方,或者自己该做的做了,其他不要计较,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可惜到最后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是你…爱的太重?”
“嗯,我也这么想,给别人压力太大?其实我也知道是需要距离的,距离产生美嘛,可是还是做不到,希望她们好,不用为谁总是受伤,不用为谁总是难过,可是她们并不接受我这样的一个人,也可以说,对于没有什么前提就自动送上来的帮助关怀,她们并不在意,不会珍惜,她们只频繁地往返于她们所不能触及的情感和物质上,乐此不疲,求而不得的苦恼。就是这样。”
“……”
“所以我想关于‘无望’,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潜意识里才发生的?真的,木木,看到了什么,然后开始极端的抵制了,既然得不到,就不再想要去要求……可是我依然希望有朋友,真的,不是矫情,我是真的想要那么一个朋友,我不漠视友情,我只是想,有那么一个朋友,平时会和你没心没肺地开玩笑,当你难过时候又可以和你坐一起听你讲心事。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难受。”
“这个不是期望了么?所以我说,你不像是得了这病的人。”
“嗯,只要记到,终会明了…”
“又来了。”
“呵呵你就将就一下,是时候的话就明白了,那你呢木木,有朋友没?”
“有…”说这话的时候我竟然底气不足,想起刚刚说我的小军,“有个十七年的朋友,小军,你认识,班上的那个。”
“真好啊,羡慕。”她往椅背上靠过去,真的是满脸羡慕。
“很不错?”
“当然,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一个人,就能理解了…话说回来,你就没觉得很有价值很不容易?”
“……嗯,是吧,”
“听我说木木,拥有的时候不在意,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这个……是屁话。”
“哈?”我满意为她搬出这条是拿来劝我什么,结果她竟然话锋一转炮轰这条被多数人津津乐道的至理名言。
“‘珍惜’是在还拥有的情况下能做的,失去了过后,不能再珍惜,你只能叹息,已经没有珍惜的基础了。”竟然很正经地开始说话,我一下回不过神。
“所以我想,‘经历是一笔财富’这个也一样,没有对自己的经历进行思考的话,那它们就仅仅是经历,变不了财富,非得你从中悟出什么道理了,它们才开始变得有价值…”她低头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和开先的她盘若两人,说完转头看了看外面,起身说,“太阳没了,咱们走吧。”
我应着起身跟她走了出去,站在店门口她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又开始笑:“今天真痛快,谢你咯。”
“好像我什么都没说吧。”我耸肩。
“哪里哪里,我说了有人能听已经不错了呢…”她拍拍我的肩膀,我这才发现她几乎和我一样高,女孩子里算是高的,我仔细打量了她,淡灰无袖丝织衫,深色冲锋裤,白色运动鞋,身材高挑,瘦弱,手指修长,短发,耳朵上戴着耳饰,一颗蓝色的珠子,模样清秀,眼睛下有淡蓝眼袋,总是疲惫的样子,却又总是笑,这样的一个女生让我觉得有什么我始终是模糊的,不鲜明,但又很鲜明,说不上来。
她神情淡淡,隐约地笑着,望着来往的车辆:“你知道吗木木,我觉得时间这东西,真是很抽象的东西,感觉它像是附着在各种东西上面,我已经忘了生物课上关于生命的定义了,反而觉得像是孩子那样认为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有生命的还更纯粹一些,它们都会消失的不是吗?时间附着在上面,所以指甲长了,头发也会变白,等等这样的,都是。我们有同样的时间附着在各个地方,同样的流失速度,但是总的时长却又不一样,这样才会意识到得到了,还有失去了,这样不是很好么。所以什么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失去什么,证明你曾经得到过,只是我们太狭隘,总是对于失去叫嚷,却从不知道在得到时候感恩,它们或许本不属于自己,那失去就是理所当然的,所幸还能得到,有什么好叫嚷的呢?”
“所以呢?”
“所以,我们都是尘埃。”
我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这句和上面的一席话貌似没什么关联,跨度太大,但总的说来却不无道理。
“是…”我点着头转过去看着来往的车辆,时间挤压,光影飞舞,“尘埃,时间附着的各种东西的组合体哈……我说你真的得了病么?”
“哈哈哈哈…”她弯腰笑起来,然后直起身子笑着看我,依然神秘兮兮地,“只要记到,终会明了。”
“是是是。”没奈何,“那我回去了。”
“嗯……”她点头,我转身走了几步她又在后面叫我,我停下转头问什么事,她垫了垫脚:“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木木?朋友?”
“朋友?”
“嗯,朋友。”
“嗯……”顿了顿,摇头轻笑,“不可以。”
“…哦,知道了。”意料之中一般毫无惊讶,或者早已习惯。
“因为已经是朋友了,这样。”等她发愣吧,转身走掉,一边挥手,“别给我发骚扰信息乱打电话就OK啦。”
……
我们只是尘埃,我们什么都不是。
| 不二•雪坠
回到寝室小军还是没回来,这家伙真生我气了,开了显示器,终于在空白的地方写了东西,但大多是雪凌的话,我把她的话记得很清楚,不知为什么也写了下来,有些话我并不理解,而最不能理解的,是那句“只要记到,终会明了”,她这丫头,始终有什么是模糊的,我明白不了,那所谓的“终会”,是什么时候?
热气降下来了才下楼买了晚饭,回来刚坐定,寝室电话响了。
“喂?”
“喂,林?”是阿柔。
“嗯,怎么?”
“还好?”
“好啊。”
“病也没事?”
“怎么你也知道了?”
“小军Q上说的…很担心你,下午打了几次你都不在。”我伸手拿过手机,上面10个未接电话,都是阿柔的。
“哦,下午出去没带手机。”
“嗯…现在没事了?”
“没…”
“……”
“怎么了?”
“你话始终是那么少呢…”
“嗯,性格问题吧。”
“……”
“咋了?”
“没…”
“还说没,不是在哭吧?”
“好了,没什么,倒是你怎么不好好照顾自己…”
“我没事…”
“……”
“……”
“……小林…我突然觉得累了…”苍白的声音,相当苍白。
“……”
“…有时候我在想,我对于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女朋友?我不知道还算不算…你太冷了,真的,本来应该热烈的感情到你那里,就变得没有了温度,我跟不上你的脚步,也或许是你不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你总是停在某个地方,当我想要找你的时候,我反而找不到回去的路。也不清楚你还在不在那里。”
“……”
“呵呵,我今天像是发了疯了,只是这些我从来没给你说起过,我其实真的有幻想,你能回到以前那个时候的你,可能你自己都已经不记得自己以前是什么模样,可是我记得,记的一清二楚,似乎可以永远不忘,笑容亲切,和气友善,为人真挚,虽然平时看着大大咧咧可是正经起来让人觉得好可靠好有安全感……只是我找不到了,所以就只能记得,没办法…”
“……柔…”
“我还好,你也不要太担心的,对了,过年的时候我没回去,知道吗我一个人去了郊外,北方那个时候简直冷得要死,但是那天天气很好,等我到了郊外的时候开始下雪了,不太大,很安静,我不喜欢城里的雪,搞得很脏,郊外不一样,都没动过,是最纯的状态,树上,田里,山上,都好漂亮,简直好的让人震惊,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柔软起来,就好想你可以在我身边,什么都不说,那么拉着我的手,一起陪我在雪地里站着,隔了手套,可能还是会有温暖…你可别笑我,当时就真的好想这样,真的…”
“嗯……”
“……林…”
“嗯?”
“……我还是喜欢你,这个是实话,真的,还是喜欢你,只是…也可能我会等,等到某一天,你真的明白某些,明白我们之间的感情,不再是简单的‘嗯’之类这样的,你可以说点什么,对我……或许我一直在等也说不定,呵呵,好了,就这样,我挂了…”
我没有回答,也或者没什么好回答,我说的不是她想要的什么,所以根本就没必要说。但是真的是这样么?就好像没有切身经历过别人的经历,但当别人给你说了过后,你说“我不能做什么,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就好了?大概雪凌在的话又会坏笑着说“看吧看吧又有想要‘知道了解’的期望了”。
是的,我可能还有想要了解的期望,只是没人会回答我,也或者,我也是在等,等到某一天,有人来告诉我答案,要不自己等到答案。
只要记到,终会明了。某一天。
然而某一天又是哪天?谁来告诉我?
……
| 不二•伤爱
从那天开始小军果然和我冷战,一直没有理我,我想要说什么,却又没有话头,只好作罢。
周六雪凌约了我去火车站,开先并不想去,但是又实在无聊,最后还是决定去。到了火车站在候车厅找了位子坐下,她拿出带来的画板开始素描。
“跑车站来画画?你这丫头简直…”
“怎么?”她不断地抬头看一会,又埋头画一会,“没见过在车站写生?”
“……很少。”
“很少就是有嘛。怎样木木,画得还行?”板子移过来,我看,全是一张张半成形的脸而已,老人的,小孩的,男的女的,满纸上都是。
“这啥?”
“很明显是脸咯,很像吧?”
“……”我抬头观望了一阵,眼前是奔波的人们,没有一个人的模样和她的画对上,“画的谁?”
“谁都是,你没看见么,好多人神情都太相似,无非就几种,想离开却不得不留下的,想留下却不得不离开的,想离开就真的可以离开的,还有想留下就真的可以留下的,这样。你觉得哪种是幸福?”
“又来了你,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离开不离开的。”撇嘴。
“呵呵,是么,如果是我呢,我觉得自己像是想留下却不得不离开的,真的,我想停下来,却一直就走。”
“漂泊?”
“不是,漂泊是种幸福,因为没有目的,所以可以不管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所有的快乐获得都在路上,但是我不是,我只是想找个地方而已,一直在找,答案,结果,但是最后累的不行,我对于好多事情是太多疑问了。”
“好多事情不要那么认真,顺其自然就好了吧?”
“是啊,为什么我却不会呢,这个大概是病症的原因了…”
“什么?”
“啊?没……”
她摇头笑着不再说话,下意识地在纸上继续涂抹,候车厅全是来来往往的人们,疲惫,焦急,淡然,留恋,幸福,什么都有,还有莫名其妙的光亮、莫名其妙的浑浊空气和总觉得散到无边无际却又真切的莫名其妙的声音,像是某个地方有人窃窃私语,纷纷乱。各式各样的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
“木木…”
“嗯?”
“你说为什么这里每天那么多人离开,却始终走不光呢?”抬头望着火车入站的方向…
“傻,就没人来了么?”这丫头一天到晚可真能想的。
“嗯,是…”点头,“有人来了就有人去了,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是离开,可是对于另一个地方,却是到来。”
“嗯…”
“木木有很多朋友在外地么?”
“嗯,有几个吧。”
“那暑假见面不是很好玩了?”
“这……还好吧,不过今年暑假没回去。”
“怎么?远?”
“不远,不想回去。”
“哦,我是不能回去。”
“哦?”
“没地方能回去,妈妈说了不要我,爸爸早死了,就是这样,大学开始就算逃出来,逃来南方。妈妈是个穷光蛋,但是还有爱好,那就是打我,她不把我当女儿,把我当同辈分的人,像姐妹哈哈,甚至有人给了我糖她会吃醋,好笑吧?和自己女儿吃醋,可她就是这样的人,很奇怪,或许是我抢了她的幸福,因为我是被捡来的,是个弃儿,然后爸爸不顾妈妈的反对养了我……但是我不恨她,真的,也许小时候恨过,但是现在我知道她其实也是残缺的女人,我对于她,是同情…”
她顿了顿,然后肯定地点头:“嗯没错,是同情…”
我有点晕,她笑着转头盯我:“怎么?好像电视剧哈?”
“我说,这也太那个什么了。”
“真难得,很不容易见到你吃惊的样子哦。”她转头过去笑然后又转回来,收住笑认真的看着我,“实话说吧……骗你的,上当没有哈哈哈。”
“……”
“啊对了,我有过男朋友哦,大概十几个我算算…”开始掰指头。
“哈?十几个?”
“哦错了。”
“我就说嘛。”
“应该是二十几个。”
“……”
“第一个大概是幼稚园…”
“……真早熟。”对她的话的真实性开始持怀疑态度。
“嗯,中班,算初恋么?”
“那个时候知道什么是爱么?”
“你是说爱情还是爱?”
“……”
“中班,是一起长大的,然后小学刚上就死了,车祸,当时没发觉怎么了,就是没人和我一起上学一起做游戏没人给我欺负了,但是后来发觉对他的印象越来越重,思念也是,我才知道自己是不是过早的体验了身边的人离开,真切的体验,所以对于这个就产生了什么认识…”
“你……”
“是灾星哈?我知道哈哈哈,实话说吧刚才那个…”
“还是骗我的哈?”
“对了,你变聪明了木木。”
“得了吧你有完没完。”
“好了好了,难得你今天这么有耐性,不说这些咱们聊其他的,你的什么‘正题’。”
“什么?”
“嗯,哦对了,刚才不说到男朋友么,前后确实爱过很多男孩子,全心全意的去爱,像上次和你说的那样,对他们…虽然不是每一个在形式上都是平等的,但是感情绝对是真实的,只是最后我还是被放弃了,大概都是会说和我在一起会累吧。”
“一直没安全感这样?还是你爱的太重了,负担?”
“嗯,大概是,他们不是没给我,只是他们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能知道他们在某个地方,可以想象他们现在都好,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一起,很幸福,这样就好,怎样木木?其实没自己重要的人在的城市,就是一座空城,那个地方不具有任何意义,顶多就一地名,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认识熟悉的他们在那里,听着那城市的名字都会亲切,因为他们在,他们在世界上某个角落和你一起,好好的活着,这就是一种幸福…”
“幸福…”
“嗯,幸福,幸福其实是很小的概念,只是满足愉悦之类而已,那么它可以是很短暂的,这样说就和痛苦之类一样是琐碎和经常性的,所以没必要总是抱怨身边尽是痛苦,也没理由不感恩你总在得到幸福对不对?”
“哦…”
“画画嘛…”她抬起画板看着,“曾经以为终究是乐观者的消遣,要把风干腐烂的静物画得鲜嫩欲滴,要把匆匆流逝的动态画得安然静默,但是后来发现是对心态而不是技术,我们有双眼睛,只是接纳,而思考和真正意义上的观察,确是用内心去的,而这个不单单是作画…”
“我说你,真得了病么?”比好多所谓的正常人还要正常嘛。
“只要记到,终会明了…”她笑着一字一字念道,拿了橡皮开始擦去一个个刚刚成形的脸孔,“我们走吧…”
“不是来画画么?”
“是啊,已经画了,这不完了么。”拂去橡皮的碎屑,嘴吹了两下,站起身,画板举到我面前,“怎样?”
“干净了。”
“错了,很多痕迹是擦不去的。”又递过来一些,“仔细看!”
“……你故意的。”
“哎哎,有些事情故意了都是抹不掉的,木木记好了。”拿上包冲我招手说走。
“是是是,只要记到,终会明了…很多痕迹抹不掉,记下了。”
她转身指着我大笑起来,笑个不停。
“喂,这个可是你让我记下的哎。”不理,继续笑,最后竟然笑得弯腰蹲下去。
“真是,就那么好笑?”正抱怨,看到她抬起头来,满脸的泪水。
“咋了?”这变的太快,我发愣。
“没事…”脸上挂着泪却笑着站起身,一个趔趄,马上用手捂了鼻子。
手指间浸出血来,另一只手胡乱的摸手提袋,我一看又是这情况,赶紧帮忙打开,摸出纸巾递给她,她接过来捂了鼻子,我问有没有什么要紧,她没回答,只是一直摆手,重新坐下来仰着头。换了几张纸,我正担心纸不够用,她像跑了几千米似的喘着气说没事了,我一看脸白的吓人,平时脸就白得跟纸一样,现在真成纸了。
“好了,走。”二话不说站起来就走,这女的,确实得了病么。
| 不二•忆歌
“木木这里总是没下雪吧,冬天也下不了?”坐在公车上她望着外边问我。
“大概是。”这么热的天提雪简直想象不出。
“家乡会下,有机会去看,以后你可以揭我短,说我笑起来跟哭似的…”淡淡的笑。
“刚才是真笑我?就那样?打死我都不信。”
“那不打死就信了…要听音乐?”拿下耳脉问我。
“不听,没兴趣。”
“听听看,没试过怎么知道……待会儿咱们再去个地方,不远……好听?”
“凑合,钢琴,什么名字?”
“逝去的回忆。”
“名字真怪,去哪儿?”
“去了就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不远哈?”我眯着眼睛望着眼前一大丛树林。
郊区的树林。
“还好,走。”说完开始带我穿越树林。
“怎么找到这里的?”
“碰巧,一次想跳河就来的。”
“开玩笑吧哪儿来的河?”
“对,就是玩笑。”
走了将近十分钟,眼前豁然开朗,面前真有条河,一直延伸,消失在地平线的一头。。
“怎样?”笑着转身。
“嗯,河水哗哗滴。”
“心情不好就来这里,看不到海,所以就来这里,一样的觉得什么都可以无所谓,虽然只是暂时的。”
“嗯。”
“我把爸爸的骨灰带出来,就撒在这了,本想放在家乡,但是离我太远,所以就带来了。”走到河堤上蹲下来。
“别真想跳吧。”这女生越接近越不像最初那样给人总是精神的感觉。模糊,还是模糊,彻头彻尾。
“还趁着冬天水退的差不多下去堆了个坟…”没理我,淡淡的笑,在回忆。
不好再说什么,站她旁边,一起看河水,四周空旷的发空,对岸也有树林,只是太远。
“对岸有什么?”
“树林。”
“我知道,怎么过去?”我四下望了望,“没见桥什么的。”
“……”
“怎么了?”
“……我们就是这样在此岸守望,对岸比如幸福的什么,却忘记身后曾经一摸一样的树林,我们才刚刚穿越…”
“哈?”
“以前来这里写下的,在坟的旁边写的…”
“记得真清楚…”
“嗯,一贯记得太清楚。”
“那你记得那坟在哪儿?河水下面什么位置?”
“不知道……”摇头。
“看吧…”
“但是所有的这里,都变成记忆了…”
“你这家伙太爱伤怀了…”我摇头撇嘴转身准备走掉,几乎能理解和她一起的人是怎样的感觉了。
“木木!”她急切地站起身叫住我,“听我说最后一句话,就一句。”
“什么,又是只要记到,终会明了?得了吧搞不清你哪句真哪句假了已经…”看她恳切的眼神,不好再说,“好了,说吧……”
“过去的如果没有想过纪念,那不叫回忆,只是记忆,没有温度。记住,真的。”听到她还这样说话我差点晕,不像在开玩笑,只是现在这话听着难免搞笑。
“嗯…好吧,我记下了。”
她这才笑起来,对我说走。
“你真得了病么?”
“只要记到,终会明了。”异口同声。
我就知道!
| 不二•忘夏
分手后还在回寝室的路上,雪凌就发来短信息:“这个夏天快要完结,把所有发生的忘掉好了。”
这丫头又在想什么?忘掉?刚不说记得么,走路不方便没回信息。进了寝室一看又没人,头开始无预兆的晕起来,脑部供血不足?挣扎着脱了鞋爬上床,手机又响了,还是雪凌:“还是记得吧,实在是对不起。”
拜托,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糊弄我,眼皮重得快撑不开,丢下手机沉沉地睡了过去,知觉消失前听到手机还响了那么一下……
被手机铃声吵醒,满身的汗,一看竟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喂”了一声,头还是发晕,但是十秒钟过后就立马清醒。
赶到医院病房,雪凌安静地躺在床上,似乎只是睡过去,不久前还在我面前说笑着的女生,就这么突然死了。
“你来了。”病床边的马医生见到是我,走过来站我身旁,看着雪凌,“自杀的,吃了安眠药……”
他叹了气,我沉默不语,他回身拿起一旁的什么递给我:“她留下的东西,我想是给你的。”
我接过来,是本日记。一页一页地翻,越往后越抑止不住地手指乱抖,所有她说过的话,竟然都在里面,而且都是在我和她见面的前一天,第二天要说的话几乎就已经写好!
最后一页,是她写给我的:“
木木: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原谅我用如此粗俗的套话,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来说明我已经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死了,也原谅我不告而别。我想自己真的累了,需要休息,太多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或许真的是傻,始终学不会活得理所当然,或许会给别人的生活平添一些茶余饭后的新闻笑料,说着谁谁自杀死了,再然后就是遗忘,是的,遗忘,多年以后,他们就会忘记多年前的今天,某个人死掉,因为以后的那些年当中,他们一定会看到更多人的生,还有死。他们连给自己的记忆空间摞地方以便记下身边重要的人的离去都还来不及,又怎么有多余的空间留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
所以还是那句话木木,对于不重要的人,名字毫无意义。
我反复地说着同样的话题,关于那些情感的认识,反复地说,我始终是迷惑的,我究竟是希望你记得我,还是忘掉,某个时候我强烈地希望你能记得,我害怕被遗忘,我本就是一个人,我不想一个人来,再一个人离开。可是又会觉得太过自私。
木木,珍惜你所拥有的,你本是幸福的,是你自己漠视幸福,你的父母爱护你,你的朋友认可你,你的恋人爱着你,难道是因为你俊秀智慧、成绩优异、口碑极佳?别的人纵然聪明神武,也不能替代你,纵然比你优秀,却不能和他们相知相契。不是因为你的优秀,也不是因为你的平凡,而是因为你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独一无二的家伙。所以,木木,好好的珍惜你的东西,你的幸福,在它们还在你身边的时候,这些不是煽情,你要明白,你有着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它们就是你的财富,你就是幸福的,你不该随意地漠视和丢掉它们。
佛学里,有“不二”的说法,意思是不在两极端,处中的看待周遭的东西,这样,我才会有把自己的认知要给你说的想法,而“不二”,其实是心态,不麻木,也不激进。
而写作,我想你一定会继续写下去吧,记得我给你说的画画的事情?那都是一样的,是情感的倾诉和表达,不要放弃它们,相信我木木,用手来写心,用心来看,这个世界就是世界本身,不美好,也不丑陋。但是如果你认为它们美好,那它们就会多少变得美好。
而关于亲情,关于友情,关于爱情,所有的这些认知,我都把它们写了下来,我想总会有这么一天,你会读到它们。但愿它能给你带来点什么启发。
最后,祝你幸福。
雪凌。”
我读完,依旧无语,马医生拍拍我的肩膀说出去走走,我点头应允。
“雪凌这个,我希望对你不要有过多的负面影响…”我们走到医院散心的水塘边,马医生终于开口,“……小林……嗯,可以这么称呼你?”
我点头。
“毕竟22年来,所有的患者都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
“22年,还没有人得了这病好好活着的,这个本来不该给你说,但是雪凌的事情你既然已经知道,瞒着你也没有多大意思…所有的患者都是承受不了自杀…”
“可是她自杀这个总是太…她看着很开朗…我是说就算表面上,看着都是开朗的,不像是得了‘无望’。”
“谁说的她得的是无望?”
“……哈?她的手背也有……”
“她的病症和你的恰恰相反,她是太过于期望,期望的太多这样,你们恰似处于两种极端知道吗,反应也不一样,你难道没见过她流鼻血?”
“!!!”
“雪凌之所以要把她的一些心得和认识给你说,我想大概是希望她的认识和你的能够互补,这样你可以从麻木的极端走向中间,我想是这样…”
“……”
“她没提起?那她一定是不想说了,可能真的一直都在犹豫吧,把她的认识和情感交给你,就像是让你记得,然后要连她那一份都一起活下去一样,如果不是她的这份遗物指明给你,这难题就留给我了,联系你也不方便,那天你从医院走了连号码都没给我,还好有雪凌,因为她的手机里,只有你的号码……”
……
还在犹豫没看出来么。
了解就意味着没伤害了么。
重要的人名字就不再是代号而已,因为有感情在里面。
我没有朋友。
期望,期望。
我们都是尘埃。
幸福。
木木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么?
嗯,朋友。
没有纪念,只是记忆。
全心全意地爱。
忘掉。
记得。
只要记到,终会明了。
“马医生…”
“嗯?”
我看着池塘里的红鲤鱼,一直是一副表情面对的红鲤鱼:“你记下了我的名字的吧?”
“……嗯,患者都有。”
“很好。”我转身,“麻烦你记下我的名字…”
“嗯?”
“…记下我的名字…或许我会成为22年来,第一个继续活下去的人……”
我转头微笑着看他,他发了一下愣,最后会意,笑着点了点头。
出了医院,我拿出手机,拨通。
“……喂。”终于应了,看来我以为的不可饶恕,都是自己的认定。
“喂……小军…”
“…嗯,什么事……”
“那个,方雪凌死了,自杀。”
“啊!?“惊讶过后又异常的平静,“也好,对她来说,是种解脱也说不定。”
“怎么说?”
“你不知道?她半年前开始就突然患上抑郁症,从来没和人说过话了…你在哪儿?医院?”
“……”
“你出什么事了?”
“啊不,没,医生说我的病没什么了,我说你在寝室?我听到游戏声了。”
“是啊在玩。”
“等我吧在寝室,待会儿回来,咱们喝一杯,好好聊聊,似乎很久没和你聊了?”
“……”
“有事?”
“没有,嗯,确实,很久没聊了……”
“很久了…”
“太久了……”
“那在寝室等我。我马上就回去。”
“好。”
半年没说过话了么……想了想,似乎都不重要了,摇头轻笑,点了收件箱里没有来得及看的一封短信,那个我尚未来得及保存的号码,看完,然后又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这短信,怕是以后都不会删掉了,摞个地方,留着。
里面只有四个字。
代我活着。
拨通另一个号码。
“喂,妈妈,是我。”
“儿子。”
“那个…妈妈,寒假……我准备去趟北方,见见阿柔,顺便处理些事情…”
“那你…”
“嗯处理完过后,我就回来,一起过年,你等我。”
“…好,好。你想不想吃香肠,我到时候给你做点。你好回来吃。”
“嗯,好…”
“好好保重身体听到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我知道……嗯…妈妈…”
“哎。”
“……你也好好保重身体。”
“好,妈知道。”
挂了电话,翻过手来,手背上是两个暗红色的扇形,中间一条不太清晰的杠,看着像是天平的模样。
不二么?呵呵,我说,你的手现在,是不是和普通女孩子的没什么两样了?
风吹过,竟然有丝凉意,抬头看见有黄绿的树叶掉下来,夏天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就悄悄走到了尽头。今年这里冬天会下雪么?北方肯定会的吧。下雪。
夏日已过,Autumn is fallen.
-